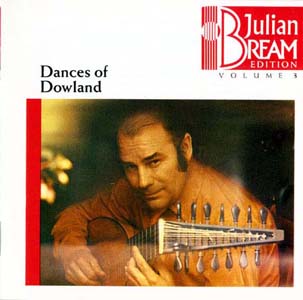巴鲁埃科访谈大卫·罗素之二
巴:你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风格,我们姑且称之为大卫·罗素风格吧。它是怎么形成的?受到那些因素的影响?
罗:谈到独特的风格,总体来说这可是个大题目,而且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发展、成长或成熟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我认为刻意去塑造你自己的风格是非常困难的。有些年轻人尝试这样去做,而且他们通常显得非常傲慢。其实马努埃你也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风格,当我从广播中听到你的演奏,我便知道那是你。这是由于熟悉使然,人们聆听你的演奏足够频繁时,便可认出你的声音。我不认为那是你能依靠主观能动去培养的某种东西。你慢慢地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你自己诠释某一乐句的方式,你自己用来区分一部古典主义音乐和一部巴洛克音乐的方法,你也意识到自己如何让它们听起来并不相同,以及当你演绎一部极具浪漫色彩的音乐时如何进行收束。你一开始当然完全是凭着感觉去弹奏,但最终你会发现其背后存在着一整套理论,你能够说出对于某个音符应该或不该在那里出现的原因。
现在回过头来回答你关于我的风格由来的问题。我生长于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我父母都是艺术家,我所有的兄弟姐妹中,除了一个之外也全都是艺术家。很多年来,我们一直象生活在大篷车中的波希米亚人一样,游徙于不同的地方。当我到伦敦去学习的时候,我非常幸运地住到一个小提琴手家中的地下室里,并学习小提琴。
我觉得有些人的个性天生就比其他人更加鲜明,这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过对于那些个性不明显的人来说,也许应该正视这一点,进行认真的思考,并找到发展个性的方法。
(对一个学生说)如果你是在想马努埃和我的情形,大概会觉得有些奇怪。马努埃生于拉丁国家,而长于说英语的美国文化中,我则是相反,来自苏格兰,但是在一个拉丁地区长大。所有这些看似平常的交融也许使你在文化等方面拥有更广泛的经历。我们都能够讲两种语言,所有这些都会对你有所帮助。你的生活阅历越是丰富多彩,你就能为你的音乐带来更多的内容。
巴:当我听你讲课的时候,你所用的一些音乐术语和语言,我从未在其他吉他教师那里听到过。这些是你从你所知的吉他圈里学到的,还是你从其他地方得知的?
罗:一堂大师班包括很多内容,尤其是考虑到同你素不相识的人只有很短的一点时间进行接触时,大师班倒更象与学生之间的一场心理游戏。你期望找到一些自己理解的东西,或者可以用来沟通的内容。帮助他人的方法多种多样,当前行之有效的方法便是从音乐上说服他们,因为我没有时间直接从技巧方面帮助他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巴:噢,当然。不过我是指你谈论的内容给我的感觉,你让我觉得你俨然是正在谈论音乐的某一位音乐家。那可不是我经常能在“吉他圈”里听到的内容。
罗:嗯,我在伦敦生活多年的圈子,并非主要由吉他家构成。不过我们必须小心,在一定程度上吉他界的确存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我不认为小提琴家或者管号类演奏家就好到哪里去,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也同样是理不清头绪。我过去曾经演奏法国号,我母亲嫁给了一个法国号演奏者,他们同样未能逃脱自身的囹圄。钢琴家也从来只是聆听钢琴音乐而对其他充耳不闻。他们或多或少都承受着与我们相同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去参加别种乐器的其他大师班,你听到他们谈论的东西虽然稍有出入,但是那些东西对于我们仍然是适用的。所以,你说的现象可能是由于我曾经弹奏过其他乐器,以及我在伦敦的社交圈和我当时的兴趣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大概是最重要的原因。
比如我曾经在西班牙的阿里坎特跟随何塞·汤马斯学习,那是非常不错的经历。他的教学方法非常直接,目的非常明确。那正是我喜欢的教学方式。“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让我经历磨炼,却从不令我意志消沉,这一点对我非常重要。他能够针对我的问题授以解决之道。教学必须是一种积极而有建设性的过程,消极的教学则毫无用处。如果你为某人弹奏之后,对方告诉你:“你的滑音不太好,但是你的颤音非常不错”,结果你回家后出于对方的反馈没有练习应该强化的滑音而是去练习颤音,这难道不是相当滑稽吗?所以我在教学过程中不管学生的水平或才能如何,我总是竭尽所能,尽量让学生不感到沮丧或者丧失信心。
巴:你觉得吉他圈内的人能够在音乐方面变得渊博多识吗?
罗:我认为可以。我觉得通过任何一种乐器都可以在音乐上变得渊博多识。我们总是倾向于说:“那要么是个吉他家,要么是个音乐家。”我觉得那是不对的,虽然事实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我认为我们小小的吉他圈有点特别,不过我想鼓励吉他手们学习至少一种其他的乐器,以期在吉他之外的音乐领域中获得一些切身体会。至少应该尝试一下室内乐。